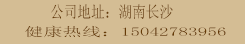按:这是《神农的退隐》第一章,共1.4万字,也全文刊出,供大家试阅。按我的写作计划,引章和第一章加起来占到全书的五分之一。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有很多动物会吃粪便。蜣螂(屎壳郎)之类的无脊椎动物就不提了,单是哺乳动物,就有很多种类都曾经被记录过吃粪便的行为。因为这一行为太常见,西方学界专门给它造了个术语叫coprophagia,来自古希腊语kopros(粪便)和phagein(吃)两词。
最为人熟知的食粪兽类自然是狗。在汉语中,“狗改不了吃屎”是家喻户晓的骂人话,形容某人秉性难移,永远改不了恶习。宠物狗主人如果看到自家的“毛孩子”吃屎,往往会非常尴尬。虽然狗吃屎的行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谜,但年的一项研究怀疑,这很可能是从狗的祖先——狼那里遗传下来的一种本能。作为群居性动物,狼会面临严重的寄生虫传染问题。群体中的病狼不可避免地会把粪便排泄在栖息地附近,如果不赶快处理掉这些粪便,狼群中的其他个体也很容易感染。狼没有人类那么聪明,只能采取一种笨方法:趁粪便还新鲜(排泄后2天内)时,把它们都吃掉。狼的主要寄生虫从卵发育为传染性幼虫的时间普遍在两天以上,在此之前把屎吃进肚子,可以让寄生虫卵被消化液杀死,不给它们发育的机会,也就斩断了传播链。虽然吃屎也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助长一些细菌性疾病的传播),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长期的演化很可能让狼养成了吃屎的天性,并把它遗传给驯化后的狗。
用这个假说来解释狗吃屎的现象,当然远不是定论。相比之下,兔子之类的兔形目(Lagomorpha)哺乳类之所以普遍会有吃屎的行为,原因就清楚多了。这些小动物会拉两种粪便,一种是干硬的普通粪便,另一种则是湿软的“盲肠便”。盲肠便是吃下去的植物性食物只消化到一半就排出的产物,其中还有没消化吸收完的养分。把它们吃下去,可以让消化过程继续进行,最终把食物中的养分充分摄取到体内。对于兔形目动物来说,这当然再划算不过了。
甚至连人类的近亲大猩猩,也偶尔会被观察到有食粪行为。对于大猩猩这样做的动机,学者们在研究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也只能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人猜测这要么是因为它们实在没事干,要么是因为想在冷天里吃口热乎东西;也有人发现大猩猩在吃过野果之后,排出的粪便里含有大量种子;就和兔子的情况一样,大猩猩把这些粪便再吃下去,可以继续消化吸收种子中的养分。
不过对人类来说,屎绝对不是食物。吃屎的行为往往是精神疾病的体现,逼人吃屎则是程度极高的凌辱。年,在香港刚刚大红大紫的年轻歌手张学友参演了王家卫执导的黑帮片《旺角卡门》,饰演小混混“乌蝇”,并因为对这一角色的出色演绎,于次年夺得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近三十年后,片中乌蝇的一个骂人表情不胫而走,成为许多网络“表情包”的素材;而乌蝇在做出这个表情时,骂的话正是“吔屎啦你!”(粤语,意即“吃屎吧你!”)
《旺角卡门》剧照
然而人类毕竟是有智慧的生物。总会有人在完全理智的情况下,做出食粪行为——比如把屎作为药物。
在中国古代如套娃一般“层累叠加”的本草书系统中,明代学者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是最后的集大成之作,李时珍也因此跻身中国古代的杰出科学家之列。由于《本草纲目》内容广泛,它传到欧洲之后,西方学者也比较重视,视为可供参考的博物学著作。甚至连达尔文,都在他讨论演化论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引用了《本草纲目》中的内容——可惜,达尔文所用的材料,是由他朋友提供的,他本人并没有亲自查阅过《本草纲目》;他甚至都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书名,只是含含糊糊地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我们无法责怪达尔文。事实上,今天大多数知道《本草纲目》和李时珍之名的中国人,也都没读过这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语)。真要去读的话,你会发现,《本草纲目》就和其他许多古代的综合性著作一样,是各种良莠不齐的材料的汇编。它真正做到了字面意义上的“把饭和屎掺在一起”。
当代著名画家蒋兆和所绘李时珍画像
《本草纲目》始刊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年),全书共52卷,除去开篇导论性质的4卷外,后面48卷共载有药物1,种,分为16部,其中矿物类4部7卷,植物(包括真菌等)类6部28卷,动物(包括人)类6部13卷。这样的分卷情况表明,自古以来,植物药在传统药材中就占据多数;不仅中医是这样,全世界其他大多数族群的传统医学也都是如此。今天的中医对《本草纲目》最看重的部分,也正是其中论植物药的部分(只有这部分的最后一卷“服器部”除外)。
相比之下,其中论动物的部分(以及“服器部”卷),今天的中医就提得比较少了,很多内容干脆视而不见。反倒是一些好事的“中医黑”,非要把其中一些不堪入目的内容摘录出来,用于取乐。这些内容里面,就包括大量有关动物屎和人屎入药的文字。
《本草纲目》中有40多种动物(包括人)的粪便可以入药,小到家蚕、木蠹虫,大到狮、虎,均有相关记载。要想从中摘出一些令人作呕的表述,那真是太容易了,比如:
用马粪并(马)齿同研烂,敷上。——这个偏方出自唐代薛弘庆《兵部手集方》,治的是“多年恶疮,或痛痒生衅”,据说“不过数次”即可痊愈。薛弘庆还说,当年诸葛亮在蜀汉做丞相,小腿上曾经长过疮,“痒不可忍”,就是用了这个办法治好的。
牛屎一块安席下,勿令母知。——这是来自唐代孟诜《食疗本草》的奇方,说的是取来一块牛屎,偷偷放在床垫下面,不要让孩子母亲知道,可以治“小儿夜啼”。
羊粪五钱,童子小便一大盏,煎六分,去滓,分三服。——这个屎尿齐下的方剂,可以治“反胃呕食”,来自北宋的官修方剂书《太平圣惠方》。
鸡矢白烧末,绵裹咬痛处,立瘥。——这是治疗牙痛的方子,是说取鸡屎(“矢”是“屎”的通假字)上面白色的部分,烧成灰,敷在痛牙上并用丝绵裹起来,马上就能治愈。方子的出处则是一本叫《经验后方》的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均已无考。
黄犬干饿数日,用生粟或米干饲之,俟其下粪,淘洗米粟令净,煮粥,入薤白一握,泡熟去薤,入沉香末二钱,食之。——这是说,先把一条黄狗饿上几天,饿到它饥不择食,见到生小米或生大米都会狼吞虎咽。然后等狗拉出其中还夹杂着未消化的米粒的屎,把其中的米粒洗净拣出(它们有个雅称叫“白龙沙”),煮成米粥,用薤白(小根蒜)和沉香末调味后,便可用于治病,治的是“噎膈不食”,也就是吞咽困难或一吃就吐。这个通过虐待动物完成的药方,出自元代的《永类钤方》。
母猪屎,水和服之。——这个简单粗暴的做法,可以“解一切毒”,而它来自大名鼎鼎的“药王”孙思邈所撰的《备急千金要方》。
马、牛、羊、鸡、狗、猪合称“六畜”。六畜之屎在历代中医药方中的应用连绵不绝,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人屎也是如此。《本草纲目》在“人部”这一卷的开篇感叹道:“(人)骨、肉、肌、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但人屎入药绝对不在“不仁”之列。因为在中医本草书的鼻祖《神农本草经》续书《名医别录》中就已经收入了人屎,而且还是“上品”。《本草纲目》中共收入人屎药方33个之多,全部取自历代方书,其中贡献最多的又是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当然李时珍也还是做了一点自己的发明,就是把“小儿胎屎”从一般的人屎中独立出来,并提供了一个新药方:为了治小儿“鬼舐头”(突然的片状脱发),可以把小儿胎屎烧成灰,与农历腊月宰杀的年猪的猪油调和,涂在患处即可。
摘录出这些古怪污秽的药方,光是为了嘲笑古人,其实没什么意思。更值得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医要用屎入药?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把中医放一放,去打量另一个古老的国度。
***
年7月中旬的一天,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西北角一个叫拉希德(Rashid)的港口城市附近,有一队法国士兵正在加固一个年久失修的军事堡垒,准备用来应对英军的进攻。就在清理废墟的过程中,在一位叫皮埃尔-弗朗索瓦·布夏尔(Pierre-Fran?oisBouchard)的中尉的指挥下,士兵们挖出了一块巨大的黑色石板。布夏尔上前查看,发现石板的一面刻有文字;他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马上意识到这块石板可能会有重要价值,便赶紧向上级汇报。很快,正在附近考察的法国学者米歇尔·朗克雷(MichelA.Lancret)匆匆赶来,发现石板上有3种不同的文字,其中一种是希腊文,另外两种虽然他不认识,但很可能是希腊文的译文。朗克雷迅速撰写了简报,通知驻扎在开罗的其他学者们。
拉希德是个常见的阿拉伯语人名和地名,本义为“向导”“正道指引者”。但法国人觉得它的发音很像“罗塞特”(Rosette,本义为“小蔷薇”),便用“罗塞特”称呼这座城市。这块石板很快也就被称为“罗塞特石”(PierredeRosette)。
这时候,法军在埃及已经岌岌可危。为了与英国争霸,年5月,拿破仑亲率大军远征埃及,企图控制这一从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交通要地。虽然埃及很快就被占领,但仅仅3个月后,法国海军舰队就在阿布基尔海战中被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H.Nelson)歼灭。年8月,拿破仑在匆匆看了一眼罗塞特石之后,就秘密撤离了埃及。残留的法军又苦战了两年,最终不得不投降;经过反复交涉,罗塞特石最后也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国管罗塞特叫罗塞塔(Rosetta),这块石头的正式中文名也因此叫“罗塞塔石”(Rosettastone)。年,罗塞塔石被运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现藏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引自大英博物馆 今天你去大英博物馆参观,会发现罗塞塔石就摆在一楼展厅的一个显要位置,与其他来自埃及的文物一样吸引着熙熙攘攘的游客。这块刻于公元前年的石碑确实意义重大,因为其上所刻的另外两种文字分别是古埃及语的正规字体“圣书体”(有点类似中国的小篆)和由圣书体高度简化而成的“世俗体”(类似草书),而这两种文字已经有一千多年没有任何人能读懂了。罗塞塔石的出土,对于人们重新破译古埃及文献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英语中,“罗塞塔石”后来干脆成了一个成语,比喻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理解线索的事物。
罗塞塔石的铭文摹本在欧洲学界流传开来之后,学者们马上开始破译工作。英国有个多才多艺的学者叫托马斯·杨(ThomasYoung),曾经用双缝干涉实验表明光是一种波,还研究过力学,把名字留在“杨氏模量”这个术语之中,这时也参与到罗塞塔石的破译中来,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最终是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Champollion,–)完成了关键的破译工作,商博良也因此成为“埃及学”(Egyptology)这门学问的真正奠基人。他利用其他古埃及语铭文,以及自己熟练掌握的科普特语(由古埃及语发展而来的一种现代语言)知识,从国王名字这样的专有名词入手,逐一破解了圣书体字母的发音。据说他在年完成了几个重要人名的破译之后,激动地跑到他哥哥(也是一位学者)那里,把一摞印刷的铭文摹本往地上一扔,大叫:“我办到了!”因为过于兴奋,之后他竟然连续几天头晕得站不起身。
商博良最早破译的两个人名,上为托勒密,下为克莱奥帕特拉
古埃及文字的释读,正如甲骨文的释读一样,把几千年前的古代文明世界重新呈现在现代人面前。此后,大量古埃及文字不断出土,人们对这个文明古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总的来说,古埃及是个虔诚的、政教合一的多神论国度,宗教生活在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由于埃及文明史非常漫长,从公元前32世纪的早王朝开始到公元前年晚王国的第31王朝灭亡为止,历时近三千年,其宗教和神谱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变化。一个典型例子是伊姆霍特普(Imhotep,另译“印和阗”),尽管相关记载十分缺乏,但铭文记载表明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公元前27世纪的人物,曾经负责过法老金字塔的建设。但在伊姆霍特普去世之后,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形象也像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很多人物一样“越放越大”,在两千年后干脆被彻底神化,成为古埃及医神,得到人们的祭祀和膜拜。
对古埃及医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木乃伊(做过防腐处理的干尸)及其相关物品来间接探究,另一种则是通过出土文书加以直接探究。古埃及人发明了一种很有特色的文字载体——纸草,是用莎草科植物纸莎草(学名Cyperuspapyrus)制作的。纸莎草本身用途非常广:它的茎可以用来造船,这种用很多茎秆捆绑而成的小舟是最古老的船舶类型之一;它木质化的地下茎可以制作碗之类的容器;它幼嫩茎秆中的髓甚至还可以食用,生食烤食皆宜;即使不把它当一顿饭,也可以当成甘蔗一样的零食来咀嚼,把髓汁咽下去,残渣吐出来。当然,纸莎草最知名的用途还是制造纸草。
尼罗河上游岸边的纸莎草(来自Wikimedia的公版图片)
如果略去细节,那么纸草的制作过程大致是这样:把纸莎草的茎劈成细条,并列排成一层,再在上面垂直地排出另一层。把这两层压实、干燥,就成为纸草,可以用来书写和绘画。纸草既可以做成长页,卷成“卷轴”存放,又可以像今天的图书一样,沿一边装订成册。
不过,虽然今天英文中“纸”(paper)这个词就是来自“纸草”(papyrus)一词,但按照比较主流的观点,纸草只是类似纸的制品,但不是真正的纸。真正的纸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技术要求:第一,要把造纸原料打碎成纸浆,让其中的纤维彼此分散;第二,要把一种叫“帘模”的工具浸入纸浆,捞出的时候其上就附着了一层纤维(术语叫“抄纸”),把这层纤维剥下晒干就是纸。今天的造纸术虽然已经非常先进,但仍然遵循着这两个技术。
顺便提一下:历史记载表明,东汉蔡伦在公元年所献的“蔡侯纸”,是最早满足这两个技术要求的真正的纸。因此,长期以来流行的“蔡伦造纸”的观点其实是正确的。然而,中国科技史界一些人出于“不是第一要争第一,是第一要争更古老”的心态,非要把蔡伦之前的一些明显不是用抄纸法制造的“古纸”(有的甚至可能不是纸)也当成纸,强行扩大纸的定义,把中国的造纸术提前到西汉甚至战国时期,这就带来一个严重问题:既然纸的定义可以随便更改,那纸草岂不是比中国那些“古纸”更有资格视为纸?这样的话,中国岂不就反而会丢掉“最早发明造纸术的国家”的头衔了吗?
言归正传。今天医学史界对古埃及医学的直接了解,主要来自19世纪以后陆续发现的几部纸草文书。年,美国古董商人埃德温·史密斯(EdwinSmith)买到一部纸草卷轴,其上的内容用古埃及语僧侣体(hieratic,介于圣书体和世俗体之间的过渡字体,类似于隶书)写成。这部名叫《史密斯纸草》的文书的写成时间,后来确定为大约公元前年。专业学者在释读之后,发现它竟然是一部流传了很久的古老医学著作的注本,其中系统而完整地记述了48个外伤病例的病史,每个病例都冷静地记录了伤病类型、对病人的检查、医师的诊断和预后以及治疗方法。除了少数文字涉及咒语之类巫术外,这份文书完全就是一份严肃的医案汇编。
《埃伯斯纸草》,现藏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EinsamerSchütze
Wikimedia,CCBY-SA3.0)然而在医学纸草文书中,《史密斯纸草》只是特例。其他文书的治疗方法都包含了大量巫术内容。比如–年冬天。德国埃及学家格奥尔格·埃伯斯(GeorgEbers)也购得一部纸草卷轴,这就是《埃伯斯纸草》。《埃伯斯纸草》的写成时间比《史密斯纸草》略晚,在公元前年左右。它篇幅浩大,就像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内容非常丰富。比如其中记载了大约种药物,可以组合成多种药方,制作成多种剂型。然而,其中也记载了一些明显是巫术的治疗方法——比如为了治疗弱视,《埃伯斯纸草》这样指导医师:
猪眼睛二枚;取出其中的水
真洗眼剂
铅丹
生蜂蜜
压碎,碾粉,调和,灌入病人耳中,立愈。如果你正确地做了这些事,重复下述咒语:
我已遵照指示,为病人用药。鳄鱼疲弱无力。(念两遍)
而为了治疗“眼中生翳”,另一个方子不惜用到了人屎,简直就像从《本草纲目》中摘抄的:
小儿所拉干屎
蜂蜜
与鲜奶调和,敷于眼上。
无独有偶,在可能与《史密斯纸草》同时的《赫斯特纸草》(HearstPapyrus)中,也有一个用到了人屎的巫方。为了驱逐引发疾病的恶鬼,病人不仅要吃屎,口中还得念念有词:
啊!你这男鬼或女鬼,你这匿迹者,你这隐藏在我肉中、在我这些身体部位中的东西!从我的这些肉和身体部位离开!看,我已经吃下了屎来对付你。隐藏者,快溜走!匿迹者,快滚开!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三千多年前的病人在接受这种治疗时是什么心情。然而,感谢埃及干旱的热带沙漠气候,让这些非常容易损毁的纸草文书能在古墓中保存下来,也感谢菲比·赫斯特(PhoebeHearst)这位杰出的美国女慈善家,不惜花费重金资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考古学研究和历时多年的埃及考察(《赫斯特纸草》就是在考察过程中获得的),这段来自遥远埃及的古老记录,为我们理解中医以屎入药的做法提供了有益启示。
***
为了理解古人以屎入药的做法,需要先做一些理论铺垫。
今天一提到“巫术”(magic),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觉得这是“封建迷信”,是愚蠢的东西;如果再提到“巫师”,很多人可能又会在脑海中浮现起骑扫把的女巫之类刻板形象。这些印象自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人类学家看来,不免带着一种现代人的傲慢。
年的詹姆斯·弗雷泽(公版图片)
巫术本来是个中性词,既包括造福于人的“白巫术”,也包括谋财害命的“黑巫术”。按照苏格兰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GeorgeFrazer,–)的看法,巫术是一系列体现了“巫术思维”(magicalthinking)的活动,目的是要操纵人们所想象的神秘超自然力量,让它们按巫师的主观意愿行事。
在人类学界,弗雷泽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同样大名鼎鼎的,是他用了30多年时间反复修订完善的名作《金枝》(GoldenBough)。《金枝》初版于年,到–年出第三版时,已经成为12卷5,多页的巨著。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他在年又出了精简的第四版,但仍然厚达七百多页。正如民俗学家刘魁立为第四版的一个中译本撰写的序言所说,乍一听“金枝”这个书名,很容易以为这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或者意蕴清幽的长诗”,但它其实是一部严肃的社会科学著作。
不过,这部专著的写作意图也确实独特。弗雷泽注意到,古罗马的一个地方有一种奇怪的风俗:如果一名逃亡的奴隶敢于铤而走险,成功折取祭祀森林女神狄安娜(Diana,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阿耳忒弥斯的对应神)的神庙附近一棵圣树上的枝条(“金枝”即其美称),便可以获得与守护圣树的神庙祭司决斗的权利。如果他在决斗中又能战胜并杀死祭司,便可以取而代之,成为下一任祭司和“森林之王”,过去的一切罪行都可以赦免。但自此以后,他一方面享受着这显赫的名声,一方面也提心吊胆,随时要提防下一个觊觎这一职位的逃亡奴隶孤注一掷,又取自己而代之。
为了解释这个古怪而复杂的习俗,弗雷泽查遍了当时人类学界对全世界民俗的报道,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加以分类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最终便对古罗马的这个折金枝的风俗做出了至少在他看来比较圆满的解释。比起这个最终解释来,他所建立的这个理论体系对学界的意义要大得多。弗雷泽仿佛独自一人建立了一整套从采矿、选矿、冶炼到锻造的工业体系,就为了打造一把厨刀,给自己做一顿午饭吃。比起这把刀来,他所建立的这套工业体系,更可以称得上是惠及后人。
弗雷泽有关传统社会习俗的理论并不都正确。还有一些人类学家,鄙夷他是“坐扶手椅的学者”,自己不做田野考察,靠着在图书馆中摘抄整理别人的著述做研究。然而公正地说,科学研究本来就应该从大量一手观察中提炼出理论,这也是现代科学的本质之一;不这样做的话,科学就只能沦为一种“集邮”式的消遣(这个比喻据说出自新西兰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E.Rutherford],他把一切科学分成两类——物理学和集邮。)事实表明,至少弗雷泽对于巫术的分类,是非常准确合用的,他所创造的一些术语,也一直沿用至今。
弗雷泽认为,体现在巫术活动中的巫术思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相似律(lawofsimilarity),也就是被人们视为相同或相似的东西,会遵循相同的运动规律;另一大类叫接触律(lawofcontact)或触染律(lawofcontagion),也就是曾经接触过的物体在相互分开之后还会继续保持远距离的相互作用。根据相似律思维执行的巫术叫顺势巫术(homeopathicmagic)或模仿巫术(imitativemagic),根据接触律思维执行的巫术叫接触巫术(contagiousmagic),二者统称“交感巫术”(sympatheticmagic)。
当然,这只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相似律还是接触律,在实际应用时,都有着大量具体的表现形式。比如顺势巫术的最典型做法是,做一个目标事物的模型,这个模型会被视为与原型等同,于是对这个模型所做的事情,也都会应验在其原型之上。因此,如果用纸做一个小人,在上面写上仇人的名字,或是贴上仇人的照片,按照巫术思维,这个小人便可以视为与仇人同一,于是对小人加以诅咒,或者用针刺扎,便可以让仇人遭受真正的灾难。西汉时曾经有过一场名为“巫蛊之祸”的宫廷内斗,汉武帝的太子刘据被人告发制作代表父皇的木头人,加以诅咒,刘据不得已起兵反抗,最后被杀,汉武帝一怒之下大开杀戒,据说死者多达数万人——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结果最惨烈的“扎小人”式巫术了。
一个用毛线做的巫蛊小人,扎了58根大头针(BeatrixBelibaste
Wikimedia,CCBY-SA3.0)而在医学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相似律思维,叫“法象药理”(thedoctrineofsignatures)。其基本原理是,如果某种药材在某个特征(通常是形状)上与人体的某个特征相似,那么把这种药材用到人身上,就有助于让人体的那个特征得到正常发挥。比如“吃核桃仁可以补脑”,就是来自西方传统医学的法象药理,因为核桃仁那种凹凸扭曲的形状有点像布满沟回的人脑。同样,《埃伯斯纸草》中那个治弱视的药方,之所以要用“猪眼睛二枚”,也是法象药理的体现,希望能够用猪眼补人眼。
法象药理是全世界各族群的传统医学普遍存在的相似律思维。与它同样普遍存在的是恶灵致病说(demonictheory),则是相似律思维与泛灵论(animism)结合之后的产物。首先,持这种思维的人认为万物有灵,像人一样能做善事或恶事;其次,就像恶人可以侵入他人的住处干坏事(比如入室盗窃)一样,恶灵也可以侵入人体,结果就会让人生病,而为了治这类疾病,就要把恶灵赶走。
《赫斯特纸草》中用屎驱逐恶鬼的思路,是相似律的进一步延伸。恶人虽然常做恶事,但也会讨厌污秽的环境,好比入室盗窃的小偷,面对一个遍地垃圾的宅男住所,大概也会望而却步。以此类推,侵入病人身体里的恶鬼,也会讨厌这个身体被污秽之物沾染。因此,要想把恶鬼赶走,只能让病人忍住恶心吃屎。当人屎把病人的身体弄脏之后,藏在其中的“匿迹者”便会受不了,只能溜之大吉。如果再配合专门的咒语,那祛病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
***
以人屎和动物屎之类秽物入药的作法,从古埃及以及美索不达尼亚医学开始,中间经过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传承,到文艺复兴之后在西方传统医学中仍有延续——而且不是简单的延续,完全可以称得上升华。比如年,德意志学者克里斯蒂安·弗兰茨·保利尼(ChristianFranzPaullini,–)出了一本医学著作,完整书题是:《促进健康的秽物药学:如何用大小便治愈大多数伤病》(HeilsameDreck-Apotheke:wienemlichmitKothundUrindiemeistenKrankheitenundSch?denglucklichgeheiletworden)。用粪尿治病,竟然可以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古代任何一位医学家都只能自叹弗如。
保利尼《促进健康的秽物药学》年版书影
然而,保利尼这本书确实是在严肃地探讨他所谓的“秽物药学”(Dreck-apotheke)。保利尼深知一般人会觉得屎尿恶心,所以开篇就单刀直入地写道:“人们在听说服用秽物的事情时,会感到厌恶,但我不得不在这本书中讲述这些事。”这样的坦诚开头,不仅能够引人注意,而且也能让读者做好心理准备,能够不皱眉头地继续看下去。
保利尼像李时珍一样,从古代医学典籍中搜罗了大量药方,又向农民、渔民等平民请教了不少民间偏方,然后用当时西方主流的医学思想——由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奠定、并经过基督宗教改造过的四体液说——对这些药方做了理论分析,在书中已经不见巫术实践的影子。在保利尼的理论中,引发疾病的已经不是恶灵,而是“毒”。为了对付毒病,就必须用同样“有毒”的秽物来治。这种“以毒攻毒”的理论,后来被西方传统医学界专门称之为“以同治同”(拉丁文为similiasimilibuscurantur),究其本质,仍不过是相似律的体现。说白了,保利尼的理论抛弃了具体的巫术实践,但并没有抛弃背后的巫术思维。
尽管保利尼这本书出版之后引来了很大争议,而且也很难想象会有多少人真的照他开列的药方去治病,但吊诡的是,这本书却一版再版,非常畅销。也许比起医书来,人们更愿意把它当成一种可以充当谈资的奇书。不仅如此,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保利尼还对有钱有权者做了尖刻嘲讽。他写道,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少权力和财富,他的肉身终归由秽土和粪便构成。哪怕是神职人员,包括教宗在内,在这一点上也都和一般人没有区别。而且,那些有钱人争相购买的龙涎香、麝香、灵猫香之类名贵药材,本质上也不过就是动物排泄或分泌的秽物罢了。反正都是用秽物治病,为什么不用那些不花钱就能得到的日常秽物,非要用那些“东印度和西印度的骗子们”高价兜售的珍稀秽物呢?虽然读者中未必有多少人会真心信服这种“秽物平等主义”观念,但肯定会有人觉得,这样阴阳怪气的文字读起来真过瘾。
分析至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看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医要用屎入药?——相信你会觉得,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人类虽然有着巨大的文化多样性,但表面的多样之下隐藏着同一,五花八门的思维方式背后,往往会体现出一些惊人的相似性。虽然古代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道路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从古希腊和罗马开始的欧洲文明存在很大差异,但早年同样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信仰巫术的时期。即使中国在秦朝之后进入了帝制时代,巫术仍然大量残存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同样,虽然我们尽可以历数中医的独特之处,但它早年同样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巫医不分的时期——这正是“医”这个字在古代会有以“巫”作偏旁的异体字“毉”的原因。虽然从战国时代起,医学和巫术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在医书中还是残存了大量巫术内容。从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中国人最早也是相信恶灵致病说的,而要治疗这些疾病,就得祛除恶鬼,这与古埃及人实在没什么两样。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人屎最早之所以会被中国人拿来治病,正是为了用污秽赶走盘踞人体内的恶鬼。
战国以后,中医理论开始去巫术化,极大地发展了“毒”的概念,但究其本质,恐怕不过是用“毒”代替了一部分恶灵罢了。《名医别录》之所以把人屎列为上品,说它“解诸毒”,也许奥秘就在这里。不仅如此,六畜之屎在《神农本草经》及其续增内容《名医别录》(由陶弘景最终编定)中也都已出现,虽然药效各异,但治疗的大都是“小儿惊痫”“恶疮”“妇人崩中”等症,而这些都曾经被视为典型的恶鬼侵人的疾病。以恶疮为例,虽然去巫术化的中医理论已经不再将其病因诉诸恶鬼,但这种恶灵致病说仍然保存在道教信仰中。比如南宋初年道士路时中及其弟子撰有道教法术手册《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在书中开列了“五瘟鬼”之名。其中的“中央黄瘟鬼”叫史文业,为“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痈肿”。而要想祛除这五瘟鬼及它们的鬼军导致的疾病,那就得向道士求符,或是请道士念咒、作法,等等。
不仅如此,中医在以屎入药时,往往要求“燔之”,也就是烧成灰。著名中医史家郑金生指出,这也是巫术残余的体现。一些污秽或怪诞的巫药,直接应用会让人觉得难堪,或者根本无法下咽,但把它们烧成灰,就转变成了一种外观平平、可以坦然接受和服用的形式。为什么一种东西烧成灰,功效与原来相同呢?原来这又是相似律的一种表现——只要人们认为焚烧前后的东西是同一的,拥有相同的“本质”或“灵气”,那么它们的功效也是相同的。
除了相似律之外,接触律思维在中医以屎入药时也有体现。夜明砂(蝙蝠屎)就是典型例子。
蝙蝠(Vespertiliosuperans),其粪便是夜明砂的来源之一(引自bio.bris.ac.uk网站)
在《神农本草经》中,“伏翼”(中国东部某些种类的蝙蝠)与“天鼠屎”(即夜明砂)分为两味药。伏翼“主治目瞑痒痛,……明目,夜视有精光”,这很显然是法象药理的体现,因为蝙蝠昼伏夜出,所以觉得蝙蝠视力一定好,所以吃蝙蝠可以明目(至于科学上证明蝙蝠定位靠的是声波而不是视力,那是晚到20世纪的事情了。)至于“天鼠屎”,则“主治面痈肿,……除惊悸”,算是屎类药材的通用功效,但丝毫没有提到能明目。不料后人在考证出天鼠屎就是蝙蝠屎之后,便认定它能“治目盲障翳,明目除疟”,也就是说,与蝙蝠本身的药效相同了。这背后的思维也很明显:既然蝙蝠屎是从蝙蝠身上分离出来的东西,那么蝙蝠有什么功效,蝙蝠屎自然也有什么功效。而且可能因为蝙蝠不易捕捉,但蝙蝠屎易于采集,发展到后来,蝙蝠屎的应用反而变得比蝙蝠还广。
夜明砂的这种功效,甚至可能还影响了蚕沙(家蚕屎)的功用。《神农本草经》中,蚕沙主要用于治疗“消渴,风痹”等。一直到《本草纲目》和清代医书,蚕沙的功用也主要围绕风症的治疗来发挥,即使个别药方用于治疗眼病,也都是因为感风而导致的病症。但在当代,一说到蚕沙,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装在枕头里面,用于明目。虽然这一功效在中医理论里面勉强也能说通,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当代人把夜明砂和蚕沙这两种屎混为一谈,结果便让蚕沙的功效被夜明砂“带歪了”。
由于以屎入药的巫术特性过于明显,虽然夜明砂、蚕沙、五灵脂(鼯鼠屎)以至“人中黄”(用人粪水浸过的甘草)在当代民间仍有广泛应用,但《中国药典》作为国家的权威药典,态度非常谨慎,始终未收入过这些药材。不过百密总有一疏,《中国药典》收录有“泻火明目”的中成药“黄连羊肝丸”,其中仍然用到了夜明砂。年底,新冠肺炎暴发,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病毒来自蝙蝠。鉴于采集夜明砂存在感染未知病毒的危险,《中国药典》年版删去了黄连羊肝丸,以示绝不鼓励人们用蝙蝠屎入药的决心。这样一来,我们在嘲笑印度那些企图通过饮用牛尿来治疗新冠肺炎的人(他们的逻辑是,牛在印度教中是神圣的动物,所以连牛的排泄物也有净化身心的作用,这显然又是接触律思维的体现)的时候,也就更有底气了。
最后要说的是,今天仍有人为秽物药学辩护,说现代医学的粪便菌群移植(fecalmicrobiotatransplantation)也是一种“以屎入药”,研究表明它对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确有疗效。这种在批判性思维里称为“不当类比”(falseanalogy)的逻辑谬误,再一次体现了相似律的巫术思维;对它的详细分析,就要留到后面的章节进行了。
***
我们已经讨论了太多的屎,是用现代医学的进展冲散一下这股味道的时候了。
对于“明目”这件事,现代医学才真正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中医也知道,眼病有多种病因,可能表现为相同的症状,但只有现代医学,才真正从科学原理上揭示了眼睛病变的真正机理,对眼病做出了正确的分类。
以夜盲(nyctylopia或nightblindness)为例,这是古埃及人就发现的一种症状,表现是在夜晚之类低光度环境下很难看清楚东西。现代医学揭示,夜盲在细胞学层次上的根源往往在于视杆细胞的病变。人眼后方的视网膜上有两种感知光线的细胞,其中矮粗的视锥细胞对强光敏感,而且能分辨颜色;细长的视杆细胞虽然不能感知颜色,但对弱光敏感,人类在夜间视物主要就靠它们。如果视杆细胞发生病变,强光环境下感觉还不明显,但到弱光环境下,视觉就会大受影响。
在营养不良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国家,夜盲通常是一类叫“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遗传病的主要症状之一。对于这类先天遗传病,大部分情况下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而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则往往有人因为维生素A缺乏病而患上夜盲,儿童受害常常更为严重。当然,要预防维生素A缺乏病这种“贫穷病”从理论上来说也很简单,只要定时为高危人群补充维生素A即可。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健康问题可能导致夜盲。比如一些恶性肿瘤会引发“副肿瘤性视觉综合征”,累及视网膜导致夜盲。不幸的是,还有一些治疗恶性肿瘤的药物(比如长春新碱和芬维A胺)也可能导致夜盲和其他眼部病变。只有了解了病因,才能做到有效的治疗。
维生素A有两类天然来源,一类是动物食品,特别是肝脏。另一类则是富含胡萝卜素及类似色素的植物食品,它们在人体内可以代谢为维生素A。胡萝卜素因为在胡萝卜中最早发现而得名,它在胡萝卜中含量也确实特别多(今天市面上极为常见的橙色胡萝卜,其橙色就来自β-胡萝卜素的颜色);除此之外,橙色的番薯(红薯)也富含胡萝卜素,甚至可能比胡萝卜还多。
尽管如此,因为维生素A分子结构相对简单,自从化学工程师找到了能够大规模人工合成维生素A的方法之后,它就完全成了一种价格低廉的合成药物。不过农学家也不甘示弱。20世纪初,两位德国农学家波特里库斯(I.Potrykus)和拜尔(P.Beyer)利用基因修饰技术(也叫转基因技术)培育出了“黄金大米”,让水稻可以在它的籽粒中积累β-胡萝卜素,于是让米粒呈现为金黄色。年,瑞士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又培育出第二代黄金大米,其中的胡萝卜素类色素含量更高,金黄的色泽也更深。
黄金大米与普通大米的对比(国际水稻研究所供图,CCBY-SA2.0)
“黄金大米”的培育初衷,是希望能让那些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只靠吃大米就能缓解维生素A缺乏病,而无须另外食用胡萝卜等副食或维生素A药剂(生活在富裕国家的民众可能很难想象,让那些贫穷国家的人口用这些似乎理所当然的方式补充维生素A有多困难)。为了推广黄金大米,两代培育者都放弃了专利权,允许农民们无偿种植、留种;还有国际水稻研究所等机构,也一直为黄金大米能获得批准而努力。然而遗憾的是,直到年,菲律宾才终于突破国内外的重重阻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黄金大米种植的国家。
与水稻一样,今天还有一种植物也不愿从现代医学中退隐,而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它是南美洲的解表木(学名Pilocarpusmicrophyllus)。
如果“解表木”这个中文名会让眼科医生们感到陌生的话,“毛果芸香”这个别名一定会让他们产生强烈的熟悉感,因为眼科的重要药物毛果芸香碱(pilocarpine)就是从这种植物的叶片中提取,并以这种植物命名的。然而在植物分类学看来,“毛果芸香”是一个很糟糕的名字。这种植物所在的解表木属的学名Pilocarpus由丹麦博物学家、林奈的学生瓦尔(M.H.Vahl)在年发表。不幸的是,在原始文献中,瓦尔没有给出这个属名的词源解释。后人只能猜测,它是来自古希腊语词pilos(毡,毡帽)和carpos(果实),但“毡(帽)”到底是形容什么,却没有定论。译出“毛果芸香”这个名字的人,显然是误以为“毡(帽)”是指果实有毛,于是用“毛果”来翻译,然而这个属很多种(包括解表木在内)的果实并没有毛。目前来看最合理的推测是,“毡帽”指的是其果实成熟时果皮的形状有点像古希腊人戴的毡帽。正因为如此,虽然毛果芸香碱是现在药学界的标准名称,但我在下文宁可用它非标准的音译名“匹罗卡品”。
解表木的叶,从中可提取匹罗卡品(毛果芸香碱)(来自Wikimedia的公版图片)
匹罗卡品是解表木属植物用来对付食草动物的毒药,对人类也具有神经毒性。人体内有两套不受意识主观控制的自主神经系统,即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们的功能正好相反。大略来说,交感神经的功能是让人兴奋起来,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瞳孔放大,这样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对付眼前可能损害人身安全的危险,要么战斗,要么逃走(在英文中,这两个词更为押韵——fightorflight)。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则是让人安静下来,心跳减缓,呼吸放慢,瞳孔缩小,这样可以让人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休息或消化刚吃下的食物(在英文中,“休息”和“消化”也是一对押韵词——restordigest)。
植物可以合成多种对付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的毒物,不是让人“过度兴奋”,就是让人“过度安静”,最后都会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甚至致死。匹罗卡品对付的就是副交感神经,可以刺激这套神经不断处在活动状态,产生口吐白沫、汗出如浆、支气管痉挛、心动过缓等一系列中毒症状。不过,它对付眼部肌肉的能力更强,滴入眼中不仅可以让瞳孔显著收缩,还能带动眼部其他结构发生变化,从而降低眼睛后方视网膜所受的眼中液体的压力(也就是“降眼压”)。
在人类所患的致盲性眼病中,白内障发病率高居第一;排第二的则是青光眼,这是一组通常因眼压升高压迫视网膜导致其病变的眼病。显然,治疗青光眼的关键在于降眼压,于是有这种药效的匹罗卡品就成了青光眼治疗的重要药物。在《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年版中,眼科的基本药物有16种,匹罗卡品即是其一。由于匹罗卡品分子相对比较复杂,虽然它也可以人工合成,但从解表木叶子中提取要更为经济。解表木这种被南美洲原住民用了千百年的草药,也因此成为现存的少数可以用来提取现代药物的经济作物之一。
然而,现代医学并不会就此止步。在匹罗卡品于19世纪后期用于治疗青光眼之后,药学界陆续又研发了多类能够降眼压的滴眼药物。它们有着与匹罗卡品不同的降压机理,效力更强,而且可以联合用药,取得更好效果。相比之下,匹罗卡品效力较弱,在降眼压的同时还有导致瞳孔缩小的副作用,现在已经不推荐作为青光眼治疗的一线用药。不过,因为匹罗卡品价格便宜,很多负担不起更好药物的人还是常常用它。
比起解表木来,与它同属芸香科的另一种植物——象橘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这个故事,需要从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讲起。
刘夙
转载请注明:http://www.ynyunyun.com/smsy/7900.html